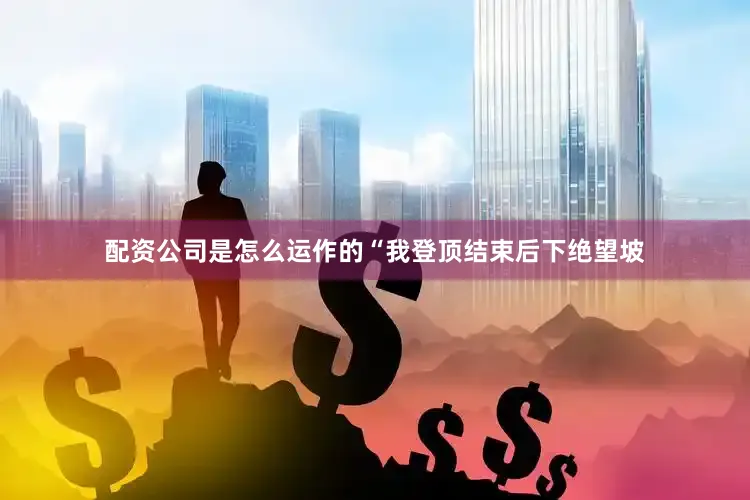每去往一座异域城市,要了解它,通常会先寻一制高点。俯瞰全城,对其地理环境、建筑风貌、街道格局等有了大概印象,再逐步进入城市的内部。可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市⸺成都,可能是对它太过熟悉的缘故,我反倒失了登高远望的冲动。直到某日,我效仿“爬楼党”,登上市中心一座四十余层高楼的屋顶,虽无睥睨天下的壮怀,但对我这个喜欢穿街走巷,习惯以平视目光打量周遭的人而言,已然惊异于眼前的景象:那些镌刻着童年往事的灰墙青瓦、梧桐荫下雾气氤氲的蜿蜒巷陌,何时被钢筋水泥的棱角吞没?眼前钢筋水泥浇铸的城市森林让我惶惑,唯见脚下一片碧玉般的绿洲⸺人民公园,这座城的记忆图腾,仍在混凝土荒原中固执地矗立着。
城市之心―― 成都人民公园,2023年 陈锦
“人民公园”原来叫“少城公园”。1911年,晚清改良浪潮中,将这片旗民禄米仓改造成成都第一座现代公园。茶馆、戏台、亭榭次第建起,门票收入成了断饷旗民的生计。竹枝词调侃:“八旗坐吃祖宗饭,提笼斗鸟丢江山;六六大顺输到底,禄米官仓变公园。”1950年,“少城公园”更名为“人民公园“,无疑是标志着社会变迁的大事件,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浓郁地域色彩的文化符号,转换成全新意识形态标识的称谓,谁能没个“解放了”的感慨呢?彼时全国城市均掀起公园更名热潮,各地都能见到“人民公园”,彰显新社会人民当家做主的自豪。更名后的这座城市公园,褪去了历史标签,却沉淀出更厚重的集体记忆。
展开剩余90%老照片唤起的共同记忆
我家书橱里有一幅老照片,照片中的母亲侧坐在草坪上,未满五岁的我和三岁的弟弟分伴母亲左右,这应该是母亲生前与我们兄弟俩最后的一张合影,不久她便因病辞世了。听父亲说这幅照片拍摄于人民公园,虽然画面中未出现公园任何标志性参照物,但我深信无误,因为母亲当年供职的四川省博物馆(现位于浣花风景名胜区的四川博物院)和我们的住家,就在人民公园内。睹物思人,每驻于照片之前总会唤起我对母亲遥远的似真似幻般的怀想。
母亲、弟弟和陈锦(左一)在成都人民公园的合影,1960年
2018年末,已八十开外的姨妈从绵阳来成都办事,抽空我们一道去逛人民公园。大约姨妈也是长时间未踏足这里了,饶有兴致地带着我寻觅当年我们在公园里的住家。我们几乎逛了一整个下午,最后停留在公园的“盆景苑”,姨妈指认这里就是那时候我们的居家处。在此之前,父亲辨认的住家又是另一处,那些年父亲晚年因罹患脑梗行动不便,我常开车载着轮椅陪他来公园转悠,每行至现在是“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的银杏阁前,父亲就会对我说:“这里从前是你妈妈办公的地方。”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人民公园应该历经多次扩建改造,有了不小的变化,四川省博物馆也于1965年搬离。作为“过来人”,除了园址和名称,谁还能说此公园仍是彼公园呢?其实,姨妈和父亲对曾经的“居家处”或“办公地”的指认是否确切无关紧要,相信驻留于他们心间的那些美好记忆早已镶嵌在了公园的每一个角落。
成都人民公园里的照相馆,2011年 陈锦
的确,记忆源自经历,个体有个体的经历,家庭有家庭的经历,社会有社会的经历。个体经历和家庭经历不可能游离于社会孤立存在,都会融入其中成为社会经历的构成部分。由此,源自经历的无数个体记忆和家庭记忆一旦在特定时代背景上互为关联,便形成整个社会成员可以共享的集体记忆。
公园茶歇,2012年 陈锦
哈布瓦赫在其著述《论集体记忆》中,将“外在唤起”作为记忆的首要条件。是的,一处遗址、一件旧物什或一幅老照片……都能唤起我们对于过往经历的记忆。但凡在成都生活过的人,无论时间长短,甚至无论进没进过人民公园,都可能与它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都可能因它唤起或多或少与自己、与家庭、与这座城市难以忘怀的记忆。前不久,我们小学同学微信群有人发了一幅梭梭板、转转椅、秋千等游乐场景的老照片,让大家伙儿猜猜是哪里。微信群里立马似开了锅,同学们争先恐后且异口同声地应答:“人民公园的儿童乐园。”接着,各自晒出了自己或家人在此游玩的留影照,并感叹这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记忆!”
茶馆里的江湖
人民(少城)公园自开园以来,曾一度成为成都最大的多功能城市文化综合体,除当年的四川省博物馆(1950年从旧皇城明远楼迁来)外,公园里还先后设立过省立图书馆、通俗教育馆、佛学社和佛经流通处、音乐演艺厅、游乐场、动物园、体育场馆、戏园、饭馆等,基本满足了市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各项需求。当然,其中数量最多、人气最旺的还是各种类型的茶馆,彰显了成都这座著名休闲城市特有的精神文化面貌。
春光烂漫的鹤鸣茶社,2021年 陈锦
川地茶馆历史悠久、数量众多,闻名遐迩,不仅是吃茶休闲之地,更具备全方位的社会功能,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大舞台和文化大舞台。有人统计民国时期公园内叫得出名的茶馆至少在六家以上:鹤鸣、枕流、绿荫阁、永聚、射德会和文化茶园等,社会上三教九流都爱在其间流连盘桓。时至今日,人民公园内茶馆尚有三家:鹤鸣、浓荫和少城苑。只要不遇刮风下雨,家家茶馆都是人头攒动,笑语欢声不绝于耳,生意好得很。曾经的“六腊战场”早已硝烟散尽,论历史最长、名气最大、茶客最多的还数鹤鸣。
鹤鸣茶社里学习汉家礼仪,2014年 陈锦
我与鹤鸣还是有些缘分的,最早源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考察、拍摄四川茶馆文化时,同吴登方师傅结识。吴登方是鹤鸣的掺茶师傅,专事为茶客掺茶续水,旧时也称堂倌或幺师。可别小看了这一角色,他们不仅需要练就一身熟稔的掺茶续水硬功夫,还得深谙人情世故,在迎来送往中与茶客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他们就是撑起茶馆“门面”、把控生意“命脉”之人。吴家爷孙三代与鹤鸣茶社结下不解之缘,经历过从早年私营到国营再到承包经营的社会变迁,堪称不同历史时期四川茶馆演化发展的见证人。
鹤鸣茶社中麻将现场教学,2018年 陈锦
过去人说四川茶馆不分什么性别、老幼、尊卑,只要你有几文铜板,都可来坐坐。旧时文化名人何满子在《蓉城忆往》中描述:“公爷们和下力的都在一家茶馆里泡,你扯你的山海经,我摆我的龙门阵,彼此无所介意,熙熙恬恬,不亦乐乎!”更有人说,要想了解或融入成都,得先从成都的茶馆坐起。看如今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除了本地老百姓喜欢光顾,还成为国内外旅游者来成都观光的“打卡”处。本地老百姓坐茶馆原本就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外地游客们来这里是为了体验一把“成都生活”,殊不知他们的行为举止也成为“成都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为四川茶馆的一道新的风景。
少城苑茶馆里的舒耳 享受,2020年 陈锦
如今七十开外的吴登方师傅从鹤鸣茶社退休赋闲已有十余年了,因吴师傅的离去加之其他俗务缠身,我也好些年头没再进过人民公园,仿佛公园于我渐行渐远。
人民的“耍相”平台
2007年,原本身体硬朗的老父亲罹患脑梗,行为自理能力受到极大影响。突如其来的变故又让我想到了人民公园,我相信公园的环境氛围有益于老父亲病体康复,也能舒缓他纠结的心绪,于是便隔三差五陪老父亲来人民公园逛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规律。
百姓秀场,2011年 陈锦
每次陪老父亲来公园总会待上一整天:上午先是用轮椅推着他四处转悠,择宽敞地儿助他拄着拐杖练习步行;晌午在鹤鸣茶社落座,泡茶,再从鹤鸣隔壁荟萃了成都各路名小吃的“钟水饺”品牌店要来他爱吃的龙抄手;歇息近下午二时,便去到浓阴处由一些中老年文艺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演出场所看唱歌跳舞;下午五时许,歌舞散场,我们回家。这个规律一直延续了好些年。与老父亲互相陪伴的这些年,我看到他沉浸于公园欢乐氛围时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愉悦,感受到他对健康的渴望及为健康付出的努力。毫无疑问,人民公园是一个帮助人们获得愉悦和制造“集体欢腾”的好去处。每次来公园看到和感受到的,总会让人思绪翻滚,仿佛周遭发生的一切,都在以特定时空中以特有方式,演绎出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随性的舞姿,2013年 陈锦
假山里的“二次元” , 2019年 陈锦
2012年,由两位国外年轻导演执导的纪录片《人民公园》“横空出世”,内容反映的正是成都人民公园。据说,该片在业界好评如潮,获奖无数。这部长达近78分钟无文字注释、无旁白解说,唯有现场声的纪录片,采用了不变焦、不切换镜头、在移动中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通过人民公园这一特定时空,自然、流畅地将成都这座城市市民恣意的“耍相”表现得妙趣横生,这种不加任何干预的真实、常态化的表达,细微、琐屑却有力量,而且意味深长。
成都当地的一个业余文艺团队会定期在公园里进行演出,深受民众的喜爱,2011年 陈锦
成都的历史悠久,人文辨识度极高。这里曾经是一座建立在个体小农经济土壤上的平民化城市,有着由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厐大市民队伍,处处充盈着浓郁的市井气息。这种市井气息衍生出来的“游戏”因子,体现在成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在这座有着深厚“市民文化”沉淀的古老城市,传统成都人的价值观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始终离不开一个“耍”字,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游戏精神”。
人在花丛中,2017年 陈锦
人民公园自然成为成都市民各式各样“耍”法传承、创新的荟萃之地。通常,每日午前,公园的游人除了例行的遛鸟、喝早茶外,就是五花八门的各种“练”了⸺大致可归为两类:健身和练歌。健身方式有摆出专业架势的行拳舞剑、跑步竞走,也有较自由且更具娱乐性的踢毽、跳绳和器械操等项目,可谓千姿百态、各臻其妙,图个环境幽静、神清气爽。声势浩大者非早晨九点至近午十一点半的练歌莫属,有专业指挥、乐队伴奏,人手一册歌本,高峰时可达数百人之众。歌者们大多是上了一些年纪的“过来人”,有着相近的人生阅历,选唱的歌曲多带有岁月痕迹,歌声真诚而饱满,仿佛就为再次邂逅逝去的青春年华,唤醒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时代记忆。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成立于中国抗战时期的故址碑,2016年 陈锦
午后至傍晚是公园最热闹的时段,遇上好天气,茶馆早已一座难求。不算大的人工湖面有无数小舟穿梭,节假日候舟人排起了长龙,舟行至逼仄处常遇“交通”拥堵。儿童乐园总是欢声鼎沸,各种玩法新旧传承、中西交融。交谊舞和广场舞定然也是少不了的,尤其后者拥有广大的群体,无男女老少之分,无熟练生疏之别,有兴趣加入便是,尽兴便是⸺舞乐无不朽的神曲,“鸟叔”走了,“小苹果”会来……永远踩着时尚与潮流的节奏。业余文艺团队演出也是一大看点,兴旺时团队多达十余支。场地不够,由公园管理方协调。各团队演出场地相距往往不过数米,为了争取观众,竞相将音箱音量调至震耳欲聋,以形成压倒之势。下午两点至五点为演出时段,节目挺丰富,演员也卖力,观众更热情,大家都快活。
公园游船,2013年 陈锦
在众多“耍相”活动中,恐怕最能够表达成都人乐天率性的生活态度,体现市井文化特色的当数关注度、参与性最高的“随意秀”。“随意秀”这一名号是我随意起的⸺因为它无固定演出场所,任何一处可以舒展手脚的空地就是“舞台”;因为它无既定的演员和观众,二者的身份随意转换,上场是演员,下场即观众;因为它无预定的场次安排、节目内容,完全是即兴创作、随意发挥。在这里,“街舞”绝不仅仅属于年轻人的专利,舞出激情来的往往是些两鬓染霜甚至耄耋之年的老者。舞姿无套路、无规则,随心而动,充分展示才艺、释放自我。其中,最有范儿的当数“闪亮登场”的走秀者。普遍认知中,走秀总是与“服饰”“潮流”“时尚”等词汇联系在一起的,强调仪式感,以体现“商品属性”为要旨。但公园里的走秀,完全颠覆了人们既往的认知,不推销任何“产品”,只为纯粹的娱人娱己。因此,走秀者们的招数出奇制胜,但凡值得博自己和观众们一乐的物件,他们都毫不“吝惜”地抖搂出来⸺装束花样迭出,扮相千奇百怪,甚至自家的锅碗瓢勺、拖把扫帚、宠物家禽等都凑上了热闹。这些走秀者们完全是以目空一切的姿态,诠释“秀”的另类美学法则和精神内核。置身于这样的秀场中,我深切感到语言的贫瘠,无法准确描述由此带来的心灵震颤。
公园一角,2013 年 陈锦
逛累了休息会儿,2013年 陈锦
人民公园的这些歌者、舞者、走秀者……用独特的“市井风”构筑的神奇景观,兴许够不上“大雅之堂”,更入不了附庸风雅者的法眼,却彰显出这座平民化城市洒脱率性和幽默达观的人文气质,以及多元、开放、包容的审美取向,尤其投合普通民众的胃口,让人民公园生机盎然,真正回归“人民”。公园原本就是市民文化的产物,其初衷就是为市民创造一个以休闲娱乐的方式逃离日常生活琐碎、宣泄内心郁闷和痛苦、享受快乐人生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各种娱乐设施、娱乐方式,各种人群都能各取所需地找到各自的娱乐项目。在人民公园这样的特定环境中,人们通过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获得快乐,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快乐相互传递、互相分享,实现体验快乐的共情与快乐体验的极致。这也是我非常愿意陪伴渐入暮年的老父亲时常来人民公园感受快乐人生的缘由。哪怕这些快乐是“快闪”式的,也是对“生命意义”的生动诠释。
陈锦
1955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毕业于云南大学。四川美术出版社原高级编辑、编审,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纪实摄影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四川省摄影家协会顾问。曾获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中国民俗摄影协会颁发的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四川省文联巴蜀文艺特别奖等重要奖项。 著有《四川茶铺》《市井》《感怀成都》和《茶铺》等图书。
本文首发于《大众摄影》杂志2025年5月刊专题“公园镜像——摄影视角、公共空间叙事和现代性图景”
发布于:四川省配资门户平台配资,在线配资交易·加杠网,天津炒股配资开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